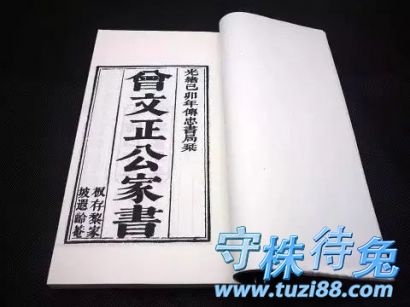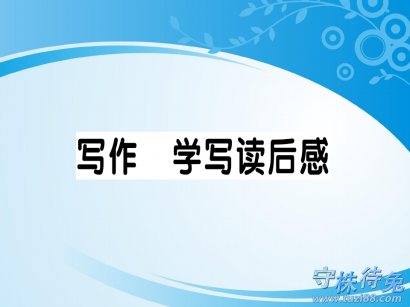《我与地坛》的母爱叙事与生命哲学
很多人知道《我与地坛》(1990年)曾被视为小说准备发表,但这一误会隐含的文学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。
这篇散文对小说笔法的借鉴,不仅涉及虚构与真实这类问题,而且指向叙事部分所使用的策略,尤其第2节对母亲的追忆,调动了现代小说关于叙述时间、叙述视角的处理手法,具有回旋往复的形式之美,而这种回旋往复,体现了史铁生在“母子”这一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中展开的哲学思考。
 一
一
现在与当年:两种时间的交错
叙事者按照时间顺序,逐步讲述事件的发生、发展与结束,由此构成线性叙事。
《秋天的怀念》(1981年)第1段脉络为:“我”双腿瘫痪—乱扔东西发泄—母亲悄悄躲出去—“我”冷静下来—母亲走进来安慰“我”。
从起因着笔,然后写母亲安慰“我”,即属于典型的线性叙事。
《我与地坛》共7节,叙事整体上基于时间顺序,但是第2节的叙述有所不同,起句就有意打破常规:
现在我才想到,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,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。
在回忆性散文中,有被回忆的过去,也有回忆过去的现在。
按照线性叙事,可以从过去写到现在,或者站在现在追忆过去,比如上面这个句子可以写成:“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,给母亲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”《我与地坛》把“现在”与“当年”“曾经”并置于三个分句的开头,不仅突出不同的时间,而且使“现在”主动参与到对“当年”与“曾经”的追忆之中。
“当年”这个词语出现的时候,往往暗示着与此不同的“现在”。
这里也不例外,“当年”与“现在”的对比意味着,在现在之前的漫长的过去,“我”其实根本没有为母亲想过,更谈不上站在母亲的角度去看待当年发生的一切。
“曾经”并非可有可无,它表明“我”“总是”跑到地坛,造成母亲“总是”默默忍受不为人知的恐惧和煎熬。
从时态上看,“当年”与“曾经”属于同样的过去,“曾经”把“我”到地坛的行为的过去时进一步拉长、延伸。
现在的强烈参与,与被拉长了的过去,在叙述上构成两种时间的交错。
在《我与地坛》中,“当年”和“曾经”是叙述的主要立足点,叙述者大部分都站在这个时间点展开叙述。
相对于“当年”和“曾经”,“现在”属于将来,因此“现在我才想到”等于把未来的事情提前说出,即格非所说的“提前叙事”或“中间叙事”。
无论是提前叙事还是中间叙事,都致力于打破时间的线性序列,把不同时间的事件集中在一起,使现在与过去交错呈现。
第2节中,这种交错叙事的句子多次出现,又往往处于结构上的关键处,如第2段以“这以后她会怎样,当年我不曾想过”为结尾,与“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,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……”相呼应,一反一正,带出第3段的整体叙事。
叙事上时间交错的写法并不鲜见,不过把它放在全部叙事的开头或结尾,通过不断涌出的时间性语词,传达某种复杂的人生况味的写法,很可能受到现代小说《百年孤独》的影响:“多年以后,面对行刑队,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”人的生存时间不同于单向流动的物理时间,它是三个时间维度——过去、现在和将来——的相互交错。
在同样叙述母爱的《合欢树》(1985年)中,全文也以时间的交错收束:“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,会想起童年的事,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,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。
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。
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,是怎么种的。
”
在不断涌出的时间性语词中,我们体会到,过去不是被偶尔拾起的碎片,而是时刻铭记在心、影响至今的精神事件。
《我与地坛》通过两种叙事时间的交错并置,把读者的注意力从“我”到地坛、母亲担忧等事件,转向这些事件在时间序列上的本质关系。
对已然不能行走的史铁生来说,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?母爱叙事不是史铁生兴之所至,而是其写作的基本动力,也是全部哲思的活水源头。
母亲对儿子未来死亡的恐惧,超过了对自己患病将死的恐惧。
母亲对当下的苦难和未来的死亡,并不是以当下个体的方式来承受,而是以朝向家庭未来的方式来克服。
为儿女而活,为儿女的美好未来而活——这一执着的念头使母亲先行到儿子幸福生活的未来,并赋予母亲坚守当下、死而后已的不屈意志。
史铁生的全部写作,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史铁生这个人的生命,源自对母亲形象的顽强追忆,源自在追忆中饱含的哀痛、呼告与希望:“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,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:母亲,她并没有死,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,对我,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,完全地失望了……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,驱之不去,我便在醒来时、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:母亲,她的灵魂并未消散,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,直等到我的眺望在幽冥中与她汇合,她才放了心,重新投生别处,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。
”(《有关庙的回忆》,1999年)
 二
二
知道与看见:两重视角的分合
《合欢树》从“十岁那年”着笔,从到“二十岁”写到“三十岁时”,都是通过“我”的眼睛来观察和记录事件。
“我”是史铁生母爱叙事的常规视角,《我与地坛》并不例外:
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,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,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。
“我”被反复提及,是因为叙事视角需要特别强调。
此话的表层意思是“我”希望母亲好好活着,看到儿子最终找到了出路,而深层意思则要倒过来读:“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”—“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”—“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”,也就是说,“我”希望母亲依然在世并为儿子的成功而骄傲,构成了史铁生踏上文学之路从而寻找生存依据的根本原因。
值得注意的是,以“我”为视角的叙事,始终伴随着“她”对“我”的凝视。
纵然躯体残缺不堪,但父母对自己的牵挂和担忧未曾退场,所以“我”必须爱护自己,尽力实现生命的价值,让自我挺立于天地之间,使之无愧于养育自己的父母——“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”。
母亲看待儿子的视角与方式,深深影响了史铁生生存与写作的方式,换言之,母亲视角早已渗入“我”的叙事视角。
接下来的第2、3段,直接切换到母亲视角:
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,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,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,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。
“知道”在第2段共出现6次,加上“担心”和“料想”等词语,形成一种单调的“她知道”“她不知道”“她料想”的句式。
较之第1节描写地坛时灵活多变的句法,这种单调句式的反复显然是叙事者刻意为之——极力把叙事视角从“我”转移到“她”,从而在第2、3两段对母亲的复杂心理活动展开多层次描写。
母亲理解双腿残疾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,也明白人生的出路只能靠儿子自己去找,但又感到儿子也许摇着轮椅就此不回,并为这个不宜问、不敢问的念头而痛苦和恐惧。
第3段以“这样一个母亲,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”收束,再次彰显母亲这一非常规的叙事视角。
与《合欢树》等文本中纪实性的叙事有所不同,《我与地坛》基于母亲视角的大量心理活动描写,来自多年以后儿子对母亲的想象与推测,实际上已经渗入小说笔法,属于文学虚构。
上文所说的母亲视角,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儿子视角而重构出来的。
前8段大体按照母与子分视角叙述,第8段则把分开了的视角重新结合:
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,她视力不好,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,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,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,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。
“看见”和“看”出现8次之多,加上意义相近的“张望”和“寻找”,造成的语义重复比第2段的“知道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同时,“她没看见我时……”以下三个分句不加逗号,一气读来颇有“她看见我看见她”的循环往复之感。
这是母子两重视角的“合”,在表面的“合”下却是“分”,即儿子故意回避母亲寻找的目光,表现为三组语词的错位:没看见/看见、看见/不去看、再抬头看/看不见(离去)。
母亲的看,是牵挂儿子是否“好好”地在地坛里,这是始终聚焦在儿子身上的视角;儿子的看,是对母亲之看的再看,但这目光游移不定,不断在“已经看见”“不去看”和“再抬头看”之间徘徊。
钱理群对鲁迅小说中“看客”与“看‘看客’”有十分精彩的分析,而在《我与地坛》这里,如果说当年的“我”是一“看客”,那么把这一“看客”叙述出来、将自身作为对立面冷静审视的,则是多年之后“看‘看客’”的“我”。
英文中表示看见的“see”有知道、理解之义,其实此处的“看见”与“知道”亦为同义。
“知道”指人对某件事的明白、了解,表示人的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,即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。
因此,《我与地坛》对叙事视角的讲究,表明母亲的故事是在“我”探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呈现的,母爱叙事被纳入“我”的个体意识的变化之中。
人类的个体意识在幼儿阶段浮现,而后逐渐增强,进而推己及人,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等关系中确证自我的存在。
双腿瘫痪把史铁生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小小的轮椅之中,个体意识被极大强化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扭曲。
在青年史铁生的眼里,只有自己,只有当下,容不下他人,也看不到过去和未来。
然而,“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,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,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,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,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,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”,他第一次发现,在我们被困于黑暗之中、没有反思意识的过去,原来早已领受了母亲深远宏大的恩惠——对儿子的忧虑、筹划和希望——而正是这种恩惠才令我们得以存在,并持续影响和塑造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。
史铁生的全部写作扎根于母爱叙事,也可以视为对逝去的母爱的回应。
记忆力和想象力也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增强发展,这使个体意识能够保持已经过去了的生活经验,更能通过换位想象,以母亲视角重新激活一度消逝的慈爱的体验。
 三
三
车辙与脚印:两代生命的缠绕
我放下书,想,这么大一座园子,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,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。
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,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,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
园子、路、车辙、脚印等词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。
车辙是轮椅车轮碾在地上留下的印痕,也象征“我”艰难走过的心路;脚印是母亲担忧寻找“我”的证明,象征她为挽救儿子而经历的短暂人生。
这里不仅以物象征,还利用象征之间的关系叙述事件,由此形成象征叙事: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,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。
很少有人关注此处的象征叙事,也很少有评论触及“车辙”与“脚印”象征的人类亲子关系及其哲理,甚至有人认为第2节仅仅抒写母爱,并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哲理。
然而,亲子关系是整个人类延续、传承的根基,从中可以窥见人性的奥秘与人类独特的生存结构,因此它的哲学意义不言而喻。
双腿瘫痪使人失去下肢的运动能力,让病患对他人产生相当程度的依赖。
如果病患是一位成年人,它还严重损伤乃至完全剥夺其自尊——某些方面,他就像婴儿一样需要父母,父母必须再一次肩负起抚养照料的责任。
“我”与母亲并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,而更像不成熟的婴儿与抚养者之间的关系。
人类学研究表明,由于直立行走导致的提前出生,人类婴儿从神经学上来看是未完成的,因而无法协调一些涉及基本生存的肌肉运动,这就要求抚养者长时间完全投入,甚至要对原来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,比如结成夫妇、组织家庭,否则婴儿随时可能死亡。
[1]就此而言,“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”叙述了史铁生丧失生活能力而重新依赖母亲的特殊遭遇,更唤醒人们对唇齿相依、生死与共的“三年免于父母之怀”的普遍回忆。
人的记忆力、想象力与个体意识,以及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,就来自婴儿的柔弱导致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形式之中。
当儿女遇到类似的重大挫折时,父母普遍具有一种相同的想法:此病虽是后天造成,但终究要怪自己没给孩子一副健全的体魄,使他难以承负人生的辛劳,最终造成终身的痛苦。
子女的残缺亦是父母终身之遗憾。
可是,谁能给残缺和健全设立一个绝对的标准呢?在史铁生笔下,有地坛中漂亮却生来弱智的小姑娘,还有扒车摔下导致四肢渐渐萎缩的7岁男孩(《我21岁那年》,1990年),然而就是这样“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”,却活出了生命应有的庄严,给儿子留下的印象如此鲜明深刻、感人至深,并在儿子“为了让她骄傲”的奋发中参与到他的写作之中,从而在儿子的希望中活在未来。
追念母爱为指向过去,让母亲骄傲则指向未来,此即“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者”(《太史公自序》)。
“孝”乃会意字,金文写作 ,上为“老”,表示父母或更老的直系亲属;下为“子”,表示儿女或直系晚辈。
,上为“老”,表示父母或更老的直系亲属;下为“子”,表示儿女或直系晚辈。
子在下,父母在上,表示子女善于侍奉父母,该字的构造生动体现了“车辙”与“脚印”所象征的亲子间互相需要、互相缠绕的生命关系。
对史铁生来说,母亲的忘我付出使这一关系持续存在,使其得以构建深远的人性视野,打开叙事空间,从而以从容的态度俯瞰人世百态,在地坛中充分展开哲学的沉思。
人的幸福最终取决于生命的自由存在,这个生命并不是孤立的,而是首先与赐予这个生命的生命缠绕在一起,因而具有超个体的时间性和历史性——“人是时间性的存在者”(海德格尔)。
只要人们依然置身于亲子关系中,无论残缺或健全,无论贫穷或富有,人生的意义就不局限于个体短暂的一生,还从根本上涉及悠远的过去与未来。
附记: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。
参考文献:
[1]张祥龙.家与孝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7:97.